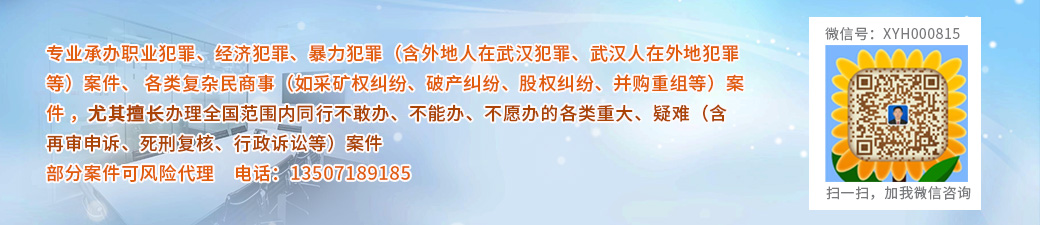从王某运输毒品罪一案谈毒品犯罪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6章第7节对毒品犯罪作了专门的规定,该节共9条,12种罪名。所谓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从广义上讲,能够证明毒品犯罪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毒品犯罪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毒品犯罪的证据也包括这些证据形式。
毒品犯罪属隐蔽型犯罪,它不像暴力型犯罪那样有明显的作案现场和痕迹。因此毒品犯罪在取证方面有以下特点:取证过程比较复杂;犯罪手段技术性强,很难追缉和取证;毒品犯罪难以获得直接证据。
但同时,基于辩护人职责,我们必需强调的是:正因为本罪处罚的严厉性,也势必要求我们认定本罪时,必需更加慎重,对证据的要求更加严格。因为,一旦在定罪量刑上有所疏忽或错误,给被告人带来的影响将是极其巨大和难以挽回的。
以我们办理的王某运输毒品罪一案为例:
2010年2月,王某独自去云南旅游,在到达广西南宁后,在一租车行租赁一辆现代轿车,前往云南景洪游玩。到达景洪后,在当地一景点(大佛寺)偶遇其一在仙桃认识的朋友李某,两人便相约一起乘坐王某租赁的现代车,先回南宁还车而后一起回湖北。途经云南省富宁县时,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到此时,王某才知道,李某并非一人,李某另有同伙李某军、张某、胡某三人,乘坐一辆三菱车,装载两提包毒品,跟随其后。该四人实为运输毒品回湖北。李某乘坐王某车辆与其同行,不过是借此为掩护,在前为后车探路。后经公安机关鉴定,两提包毒品为冰毒,净重11150克。
而依据现有证据,我们认为,公诉人指控王某犯罪证据不足,王某应属无罪,并提出如下辩护理由。
一、关于王某去云南的目的。
起诉书指控王某是在绰号 “小陈”的男子邀约下到达云南,并试图以此说明王某去云南的主观意图为“帮小陈运输毒品回湖北”。
但,本案中“小陈”在逃,其真实身份、姓甚名谁,我们毫不知情,甚至连是否确有其人都无法准确判定。虽然,本案其它被告人均谈到“小陈”。但,王某坚决否认认识此人,更谈不上受其邀约。其它被告人的供述即便真实,也只能证明他们本人是受“小陈”邀约和指挥,却无法证实王某去云南也系受“小陈”邀约。
因此,我们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某去云南的原因为运输毒品,只能证明王某为旅游前往云南,而这直接关系到王某主观动机,是本案关键事实之一。
二、关于王某运输毒品的行为。
本案中有关运输毒品的过程,以2010年2月7日为节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月7日之前、2月7日当天、2月7日之后。
1、2月7日之前
王某坚持其独自前往云南的供述。
李某等四人,承认是在受到“小陈”分别、单独的邀约下去到云南。并且供述,四人在到达云南以后,各自单独居住,并未在一起为本案进行聚集或谋划。
同时,王某没有任何涉毒犯罪前科,与李某等人也认识不久,不存在与李某等人具有犯意上的默契而无需通谋的前提条件。
那么,即然王某为旅游来到云南,到达云南后也没有与其余四被告进行联系、交往、合谋,当然就无法得知其余四人运输毒品的真实目的或产生与其余四人共同的犯意。
因此,我们认为,王某在2月7日之前,其本人没有运输毒品的主观故意,也不清楚其余四人的真实目的。
2、2月7日当天
①2月7日是李某等人取到毒品并出发的时间。王某有无取到毒品,并放至运输毒品的三凌汽车上,是本案的关键事实。
关于这一重要情节,全案只有李某一人供述。
李某供述称“2009年2月7日,小陈电话通知其与一叫阿远的人联系,李某与阿远联系后,阿远将其带到景洪江北北岸康城,并给李某一把房间钥匙,叫其去1307号房间拿毒品,之后阿远就走了。李某便打电话让王某,让王某上楼去拿毒品,之后李某也走了。过了一会儿王某打电话来说拿到了毒品,并已给李某军等三人了……小陈电话不记得,存放毒品房间的门钥匙也扔了”。
上述情况,李某并非亲眼目暏,而是由电话听闻,不属直接证据。
同时,对于上述供述,全案没有任何其它人证、物证相映证,有的证据更与该供述相矛盾,无法形成证据链。因此仅凭这一单一证据,无法证明王某取毒品、交毒品的重要事实。
李某供述,取毒品是阿远直接安排的,但这个阿远并未到案,本案其余四人均未与其接触,只有李某一人提到此人。那么,阿远是否真有其人,李某供述是否属实,有无可能就是李某取的毒品,这些疑问我们即无法排除,又无法核实。
李某供述,王某在电话中告知其已取到毒品,并已交给李某军、张某、胡某三人。但李某军等三人的供述却与此相矛盾。
李某军供述“其在景洪上车时并没有注意到三凌车上有毒品,到了思茅的银耳县,才看见车上有两个提包装满了毒品”。
张某供述“胡某开车过来,他就上了胡某的车,不知道是谁将毒品放在车上的”。
胡某供述“2010年2月7日晚7点钟,一叫卫阳的老乡拿车钥匙给我说,从昆明租下来的三凌车在宾馆停车场里,叫我开车去接两个人,后就出发回湖北。我去停车场时发现车的后备箱里有两个包,我问他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是毒品”。
根据李某军等三人供述,他们并不清楚三凌车上的两提包毒品是谁放上去的。也就是说他们三人中,没有任何人接到过王某交来的毒品。因此,李某的供述与李某军三人的供述是相互矛盾的,不能得出由王某交毒品的结论。
同时,李某供述“在王某取毒品时,我打电话给小勇、爱军、老胡三人,分别把卡给他们,并和他们商量晚上走,还是哪时走比较好,和他们用电话相互商量后,都说晚上走比较安全,并且由我和虎子坐现代车在前带路,主要负责探路,每融10分钟打一次电话,如果不打电话,就发短信,如好就是安全,商量好后,我就叫他们等起,我回宾馆了。”
从这一供述分析:在李某与李某军三人联系时,王某不在现场,没有参与协商,因此王某不知道李某军三人新的联系方式。同时,李某也未向王某告知其余三人的联系方式或接头地点,其余三人也没有与王某联系。因此,王某在即无联系方式,又无接头地点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将毒品交到李某军等三人手上。
胡某的供述可为我们指出另一可能性----毒品是卫阳的亲戚取来放到三凌车的。从其供述来看,三凌车车钥匙是卫阳亲戚交给他的,而他在取车后即发现装毒品的提包在车上。显然,车在交给胡某之前,是处于卫阳亲戚控制之下。因此,本案也存在,由卫阳亲戚取毒品并放到三凌车上的可能。
至于,公诉机关关于“王某将毒品交给了一个“不知名”的男子转交给胡某”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断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胡某供述提到,给他车钥匙的、称为“卫阳老乡”的人,小名叫小天,是湖北仙桃人,和给他新电话卡的人是同一人。而本案被告李某,小名也叫小天,也是湖北人,给新电话卡的也是李某。那么如果是李某将装有毒品的三凌车交给胡某,则李某的供述即属虚假,毒品应由李某取来并交给胡某,而与王某无关,公诉机关的上述观点则不能成立。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关于王某取毒品、交毒品的情节没有直接证据。各间接证据间存在矛盾,不能合理排除和解释,不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不能作为认定相关情节的依据。因此,无证据证明王某有取毒品、交毒品的行为。
②2月7日李某等人出发前,王某并未参与李某等四人的合谋,对运输毒品回湖北并不知情。
上文已提到,由李某的供述得知,2月7日出发之前,王某没有参与李某等四人,就运毒品回湖北的具体路线、赶路方式、时间、分工等相关内容的合谋。
李某军、张某、胡某三人,也没有关于王某参与过此类谋划的供述,能够与李某供述相映证。
因此,应当认定,王某在2月7日当天,不仅没有取毒品、交毒品的行为。同时也没有与李某等四人,就运输毒品具体细节进行合谋的行为。
3、2月7日之后
关于王某在2月7日出发之后的情况,李某供述相互矛盾,前后不一。其先后做出过“与王某交替开车、交替向后车报告情况;王某一人开车;由王某说了算,由王某打电话通知走或停”,共三种说法。
但,王某供述,其与李某同行是为回南宁还车,并未承认其有在前探路的行为。并供述租车后都是其本人驾驶,李某不会开车。
而李某军供述“张某都不断接到李某电话,李某叫我们做什么,张某就按李某的指令做什么”。
张某供述“一路上都是李某用短信提示怎么走,并每10到20分钟打一次电话”。
从供述上来看,李某的供述不仅自相矛盾,也与其他同案犯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认定王某有探路行为的依据。相反,到可以认定是由李某在掌握着后车前进的节奏。
同时,从五人的通话记录来看。王某与李某联系较多,与张某在2010年2月8日5点至6点有过三次联系,与李某军、胡某没有联系。
王某与李某联系,由于二人同乘一车,显然不属于探路报信。与张某虽有过联系,但也存在为其它事情通话的可能,如果仅凭这三次电话就断定王某有探路的行为,过于牵强。
而李某与张某联系非常频繁,能与李某军、张某供述相映证。
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只能认定王某确有与李某同行的事实,但不能据此推论,王某即在实施探路的行为。
综合上述三个时间点的事实及证据,我们认为: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王某在2月7日之前,有与其余四人合谋运毒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王某在2月7日当天,有去北岸康城取毒品并交到三凌车上的行为,有与其余四人就运毒品回湖北具体细节进行谋划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王某在2月7日之后,有在前探路的行为。因此,不能认定王某具有明知毒品、有意运输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三、关于本案其它重要情节
1、两提包毒品是客观存在的,但即便王某确曾取过这两个提包,我们又如何能够断定,王某必然打开过提包,必定知道提包内所装物品就是毒品。
全案涉及到此重要情节的,只有李某供述。其原话为“我就叫他上楼去拿毒品……过了一会儿,王某打电话来说拿到了毒品,有贰拾块”。
上文已谈到,这一过程李某并不在场,也无其它证据能与其供述相映证。那么,王某取、交毒品的详细过程,是怎样的?其是否打开过提包?其并无吸毒、贩毒前科,如果打开,他如何判断这就是毒品?李某在上述供述中直接使用了“毒品”二字,但在其它供述中又使用过“提货”的说法,那么他是如何向王某交待的,是直接告知“毒品”二字,还是使用其它代称。王某如果打过电话,他是直接称毒品,还是使用其它代称。上述“毒品”二字是李某供述时简化的说法,还是当时的原话?
上述重要细节我们不得而知,因此也无法判断,即使王某取过两个提包,就一定知道装的是毒品。
加之,王某并未驾驶装有毒品的三凌车。据李某等四人交待,李某、王某二人与三凌车是一前一后分开行驶,停车时两车分开停放,五人住不同宾馆。这些情况,可能是犯罪份子逃避侦查的手段,但也说明王某具有确不知情的极大可能。
2、桂ALR418号现代车为王某租赁。王某租车究竟是为旅游还是为运毒,全案证据并未给我们一个交待。如为运毒,车是谁租的,租车费是谁提供的?若是他人提供,此人是谁?若是王某支付,李某供述其只给过王某2000元钱,也未替王某支付过租车费用,难道是王某自已垫付的,这又于情理上说不通。若王某一开始租车是为旅游,为什么之后会用来运毒,这一转变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
再有,“阿远”是谁,究竟有无安排李某取毒品?“卫阳”是谁,“卫阳亲戚”又是谁,是否是他将毒品放到三凌车上,王某是否有将毒品交给他的行为?北岸康城1307号房间,是否存在?属于谁?房门钥匙是否真得被扔了?如果扔了,又是被谁扔的,是李某扔的,还是王某交完毒品后扔的,亦或是王某交给李某扔的?
等等上述重要细节,直接关系到王某主观心态的认定,关系到王某对运输毒品是否明知的认定,关系到王某有无运输毒品行为的认定,是本案重要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全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答案。
四、对本案的辩护结论
辩护人认为下列法律及司法解释应当引起合议庭高度重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实施的行为是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一)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所携带的物品内查获毒品的;
(二)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三)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
(四)体内藏匿毒品的;
(五)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不等值的报酬而携带、运输毒品的;
(六)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毒品的;
(七)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的;
(八)其他有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本案控方指控证据的情况分析,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无法证明王某运输毒品的动机与目的,无法证明王某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无法证明王某明知是毒品而运输;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没有合理排除;证据不具有排它性,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的原则,辩护人主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对控方证据提出反驳和质疑,而控方就应当对这些反驳和质疑做出合理解释,否则,就说明控方证据缺乏证明力,用于指控的证据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的锁链,根本达不到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的定罪标准。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反的情况除了依法能证实无罪外,则是证据不足。对于证据不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务已经确立了有利被告解释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即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此,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我们认为,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陈述,相互印证,排除非法取证的情况下,可以定案。毒品犯罪具有交易时比较隐蔽且大都单线联系的特点,所以除查获的毒品和被告人的口供外,其他直接证据很难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案犯也属“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作证的。而且同案犯是案件的当事人,他的供述会全面、详尽地反映作案的目的、动机、手段、过程。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口供经查证属实,是定案的根据之一。《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除了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吻合,相互印证,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的,才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对以次作为定案依据,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要特别慎重。没有充分、绝对的把握,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条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不是对现有法律的突破。适用该条有“量”的规定,除被告人的供述外,还必须有同案人的供述;从“质”的方面来看,要供述吻合,并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
根据以上证据审查原则,我们认为王某运输毒品罪一案,控方提交的证据,不能相互映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认定王某构成犯罪。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最终在法院认定王某运输毒品数量达11150克的情况下,对其处以13年有期徒刑,虽未最终实现无罪判决,但就其认定数额与量刑幅度相比较,也已实现了有罪罪轻的部分辩护目的。